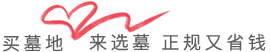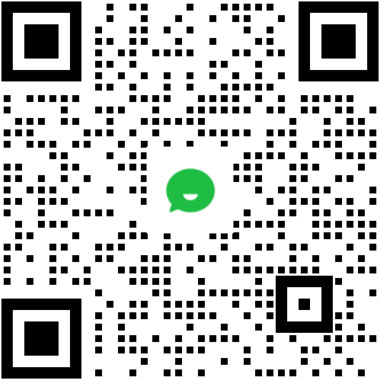这辆车穿过这座城的早晨,像一支缓慢的箭。它从钟楼附近某个站台出发,与无数赶着打卡的车流短暂同路,然后便在一个不起眼的岔路口,拐向了东南。车上的人,大多静默,手里提着的不是公文包,是几样果品,一叠纸钱,或是一束被透明塑料纸小心包裹的菊花。引擎低吼,公交车开始爬坡。车窗外的景致,从楼宇的密林,渐次变为工地、村庄、田野,最后是塬上坦荡的、被冬日阳光晒得发白的土地。不过十五公里,不过四十五分钟车程,一座城的热闹与焦灼,便被不动声色地卸在了身后。

“前方到站,白鹿原公墓。”电子女声平稳地报站,没有一丝多余的起伏。人们依次下车,走向那片整齐肃穆的碑林。那里,离司马迁笔下“披山带河”的形胜之地不远,离陈忠实先生笔下那些在塬上哭过、笑过、活过、死过的灵魂们,更近。这十五公里,于是成了一条清晰的边界,分割开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。市区的时间是向前的,是膨胀的、急促的,以发展和未来为刻度;而这里的时间,是回望的,是沉淀的、循环的,以记忆和永恒为坐标。这趟公交车,便成了穿梭于这两种时间之间的、一艘日常的摆渡船。
车上常有固定的乘客。我见过一位老先生,几乎每月都来。他总坐在靠窗的同一个位置,目光落在窗外流动的景物上,又仿佛落在更远的地方。他不与任何人交谈,只是在下车时,会对司机微微颔首,司机也回以一个心照不宣的点头。那是常客之间的默契。还有一位中年妇人,会低声对身旁空位讲述一路上看见的新变化:“你看,那里又起了新楼……咱家楼下那家泡馍馆,关啦,听说老板儿子接他去南方了……”仿佛这十五公里的路程,是她精心准备的、与另一个世界同步更新的简报。车窗外的城市飞奔,窗内的低语却执着地锚定着过去。这辆车,装载的不仅是乘客,更是无数亟待续写的对话,是亟待连接的两端。

这寻常的公交线路,无意中抚平了生死的嶙峋边界。没有灵车森然的仪式感,没有远途跋涉的艰辛与隔绝。它太日常了,日常得像一趟去郊区超市的采购,像一次去公园的漫步。正是这种日常,赋予告别一种可承受的形态。思念不必积累成一场浩大而艰难的山海远赴,它可以化整为零,变成一次心血来潮的午后出行,变成“顺路去看看”的轻易。死亡被这趟公交车,以一种朴素的方式,重新接回了生的轨道旁,成为可以定期探访的邻人。
返程时,车厢常常更安静。人们带着空了的袋子,眼角或许有未擦净的湿痕,望着窗外。夕阳把塬头的轮廓镀上金边,城市的灯光在前方地平线上渐次亮起,像一片倒悬的星海。那十五公里的归途,仿佛是一次缓慢的“再入”过程——从寂静的彼岸,重返喧嚣的人间烟火。人们带回的,是心上一小块被泪水洗净的虚空,也是被抚慰过的、可以继续前行的踏实。
所以,这辆910路公交车,究竟穿行在怎样的路途上?它驶过的是地图上确凿的十五公里,更是人心之间那些难以计量的迢遥。它是一根缝合线,将生者的市井与逝者的原野,将飞速向前的时代与深情回望的个人,将巨大的无常与琐碎的日常,温柔地缝合在一起。每一个班次,都是一次文明的微缩实践:它不鼓吹遗忘,也不沉溺于哀伤,它只是提供一种频率,一种节奏,让告别得以进行,让记忆得以呼吸,让生者与逝者在定期的重逢与告别中,彼此确认,各自安宁。
它从城市的心脏出发,开往一片高处的安宁之地;再从那片安宁之地返回,重新汇入城市奔腾的血脉。日复一日,这辆绿色的公交车,就这样在十五公里的短途上,完成着它漫长而庄严的摆渡。它让塬下的我们知道,那片高坡并不远,它就在日常生活的下一站。而我们所有的惦念,都有一班准时发出的车,可以抵达。